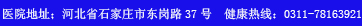悦语随笔平淡的况味读汪曾祺的鉴赏家
2022/5/19 来源:不详汪曾祺的《鉴赏家》创作于年,如朝花夕拾,平淡中自有深远之致。朴实的语言,无处不透露出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鉴赏家》是篇经典小说,代表了他以散文写小说,把风俗民情写进小说的个人风格。小说主人公叶三也代表了一个质朴,厚道,善良,对生活无比热爱,又讲究生活品质,有独到的审美眼光的小商人形象。
一、平淡的语言。
汪曾祺这个被阿城称作没有文艺味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一贯都是散文化。汪曾祺曾经说:“散文化的小说作者十分潜心于语言。他们深知,除了语言,小说就不存在。他们希望自己的语言雅致、精确、平易。”远离所谓的华丽辞藻,使他的语言干净自然,在平常中见出不平常。天然去雕饰,朴素见真美。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批把。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人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他还卖佛手、香椽。人家买去,配架装盘,书斋清供,闻香观赏。”
这段文字溢于纸面的是清香,正源于语言那朴素的清香。没有什么多余的语言,“棒打萝卜”“‘一线红’蜜桃”……却色、香、味跃然纸上,这是汪老语言的功力。朴实的语言,自然的动作,出自心田,流淌于笔端。丰富的生活,沧桑的经历,独到的追求,打造出耐人寻味不同凡响的语言,读了不能不令人惊叹汪老的老练的文笔。看似平凡语言里却处处留露出智慧的思维,不能不惊叹,妙笔高手的语言。真有十年磨一剑的功力。
二、平淡的故事。
《鉴赏家》里的人物“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一个看似很普通的一个人,但在这普通人身上,作者发现了一个成为不同寻常的人的生活细节。
“(叶三)挎着一个金丝篾篮,篮子上插一把小秤,他走进堂屋,扬声称呼主人。……他的果子的好处,第一是得四时之先。市上还没有见这种果子,他的篮子里已经有了。第二是都很大,都均匀,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全都从他手里过过,有疤的、有虫眼的、挤筐、破皮、变色、过小的全都剔下来,贱价卖给别的果贩。他的果子都是原装,有些是直接到产地采办来的,都是“树熟”,——不是在米糠里闷熟了的。”
叶三是卖果子的,他对卖果子的生活品质要求不仅丰富了个人阅历,还造就了自己成为一个鉴赏家的资质。叶三一出场就与所有卖果子的不一样。第一他的道具,金丝蔑篮,篮子里插小秤,秤好放到八仙桌上,这些考究的装饰,对果子的敬畏心情是一般人不具备的。还有他卖果子是送,要原装的,果子形状个个都是艺术品,四时之鲜个个都是“果子画”,这些不带功利的小商人品质和审美的眼光使他在送果子中扩大了视野,增加了接触名流的机会,也提高了鉴别的能力,这一切生活都为他成为鉴赏家提供了基础。
在这个以功利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叶三却把维持生活的卖果子演变成艺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艺术。看似平淡的细节中,作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
平淡事情中也有美。生活中处处都有你需要的,只是缺少发现你需要的眼睛。叶三热爱生活,时刻注意发现和欣赏新鲜活泼的生意,才能从紫藤的乱花里看出风来,才会懂得一只小老鼠的顽皮,才会知道“红花莲子白花藕”。我们在他身上发现的是对生活的真挚的爱。我们从叶三身上读到的,是对美的纯粹深沉、不涉功利的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鉴赏家之本质所在。
三、平淡的民风。
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欣赏一副淳朴风俗画。作品中显示的风土人情,民俗民风给人一种淳朴美丽的悲凉,恬淡自然美丽动人,而又让人略感悲凉的民俗民风气息。读《鉴赏家》,淳朴的民俗民风,就像一副人生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
“叶三卖了三十多年果子,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人了。他们都是学布店的,都出了师了。老二是三柜,老大已经升为二柜了。谁都认为老大将来是会升为头柜,并且会当管事的。他天生是一块好材料。他是店里头一把算盘,年终结总时总得由他坐在账房里哔哔剥剥打好几天。接待厂家的客人,研究进货(进货是个大学问,是一年的大计,下年多进哪路货,少进哪路货,哪些必须常备,哪些可以试销,关系全年的盈亏),都少不了他。老二也很能干。量布、撕布(撕布不用剪子开口,两手的两个指头夹着,借一点巧劲,嗤——的一声,布就撕到头了),干净利落。店伙的动作快慢,也是一个布店的招牌。顾客总愿意从手脚麻利的店伙手里买布。这是天分,也靠练习。有人就一辈子都是迟钝笨拙,改不过来。不管干哪一行,都是人比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弟兄俩都长得很神气,眉清目秀,不高不矮。布店的店伙穿得都很好。什么料子时新,他们就穿什么料子。他们的衣料当然是价廉物美的。他们买衣料是按进货价算的,不加利润;若是零头,还有折扣。这是布店的规矩,也是老板乐为之的,因为店伙穿得时髦,也是给店里装门面的事。有的顾客来买布,常常指着店伙的长衫或翻在外面的短衫的袖子:‘照你这样的,给我来一件。’”
这段文字写布店的,看似与主题没有什么相关性,但它们都如风俗一般,铺展开故乡风物的画卷,而人在其中,甚至可以说是处处有人。但作者并不是有意地在小说里加进风俗画,他说自己原是无意的。只是因为他的相当一部分小说都是写家乡,写小城的生活,平常的人事,每天都在发生、举止可见的小小的悲欢,这样,写进一点风俗,便是很自然的事了。“人情”和“风土”,原是紧密关联的。(《谈谈风俗画》)
作家是用疏朗的笔画、用各色水果勾勒出了一幅当地的四季风物图和一年的光景,其实这是写一种安静、适意的淳朴生活,须知“风俗即人”。更为重要的是,文字背后是作家爱怜、感慨的眼神,因为他深知“这种封闭的古铜色的生活是存留不住的”,一切都将改变。暖洋洋的抒情中深隐着汪曾祺的“人面不知何处去”的伤怀之思。汪曾祺也说到自己对于风俗的兴趣:“我对风俗有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它很美。”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谈谈风俗画》)“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四、平淡的人物。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一开篇的交代让人一震,但实际上两个人物都是平凡但有个性的人物,在平淡中见其真味。
“他(叶三)给季陶民送果子,一来就是半天。他给季陶民磨墨、漂朱膘、研石青石绿、抻纸。季陶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意,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的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也正是季陶民的得意之笔。季陶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叶三的赞赏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谀媚。”
画家季匋民与果贩叶三在他们各自的生活圈里都举止超常,这样的画家与鉴赏家的奇妙组合也极超常,在人群中他们只对彼此“另眼相看”,何以会有这另一段高山流水的知音传奇?显然是因为士的血脉让他们不约而同地跳出商业重围,暂时避进传统文化艺术的幽静,尽量不受商业惊动。他们的相遇,他们的惺惺相惜,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心灵选择和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这两个古朴的人物身上,汪曾祺寄寓着一种无比深厚的人文理想。而汪氏自己也一直效仿季氏的“荷梗甚长,一笔到底”,他画的花全是“杆子都这么老长”。“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从某种意义上说,《鉴赏家》生动地展现了士被繁华、被世俗边缘化的艰难处境。
《鉴赏家》平淡的人,平常的事,平凡的生活,平实质朴的文风,作者给我们娓娓到来,如诉家珍,在平淡中让我们感受到生活中的美,也让我们领悟到真正的艺术家来自生活,真正的艺术是最纯粹最本真的美的理解。
悦语初心
行则将至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